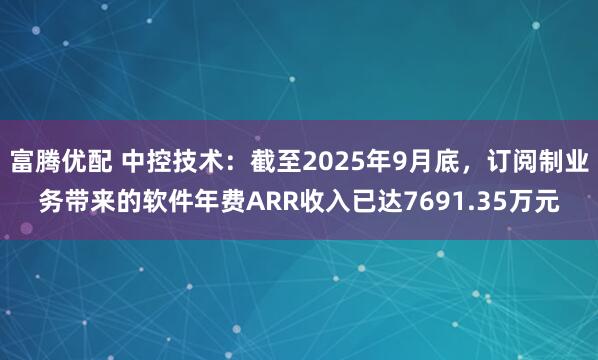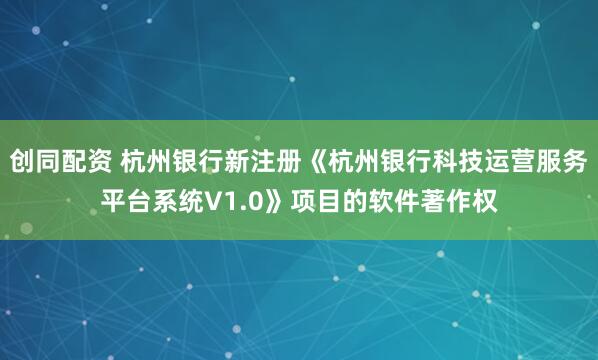1934年10月21日凌晨天通盈,赣南信丰百石村薄雾翻涌,红四师的先头部队踩着湿漉漉的山路摸向敌碉堡。一名只剩右臂的年轻师长举着指挥刀,低声吼出一句“跟我上”,火光瞬间点燃黑夜。枪声、呐喊、泥浆,交织成一片,百石关口被撕开。
子弹呼啸贴着耳边飞。洪超冲在最前,贴身观察守军火力点,他熟得像在自家院子里走动。迫击炮调整角度的空当,他突然被流弹击中额角,鲜血顺着脸颊往下淌。警卫员扑过去,他摆了摆手:“先打完仗。”声音嘶哑,却压得住场面。
黄克诚赶来,只听洪超又重复一句:“不要管我,踢开这块绊脚石。”话尾刚落,头微微一偏,25岁的生命定格在泥水里。三小时后,百石守军全部被歼,战士们抱着热乎乎的枪管才发现师长已离去。有人低声念叨:“他还欠自己一条完整的左臂。”话音颤抖。
时间跳到1974年11月,首都解放军总医院。彭德怀病榻前,呼吸微弱,他抓着护士的袖口,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嘱咐:“不要忘记洪超,他是我们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。”医护人员对这个名字并不熟,可老帅的手指在颤,没人再追问。床头灯光下,那句话沉得像铅块。

洪超究竟是哪路英雄,能让彭德怀四十年后仍记挂?答案要回到黄梅县新水乡。1909年,他出生在一间破瓦屋里,六岁丧父天通盈,九岁母改嫁,祖孙俩靠挖野菜度日。讨过饭,当过纱厂童工,胳膊上留下烙铁疤。早熟的孩子很快学会一件事:活下去要硬。
17岁那年,洪超跟着家乡农运骨干贴标语、分借谷,扛起梭镖站夜岗,被地主团丁捉进祠堂吊打时,他死咬木棍没吭声。地下党趁夜救出他,转送到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队。教室里还坐着一个身材瘦高的青年——粟裕。队里训话多半以“活捉军阀”开头,洪超听得血脉贲张。

1927年之后,南昌、广州、湘南三次起义都有他,朱德带队上井冈时,将这个灵活的小伙子留下当警卫班长。井冈山的反“会剿”屡见火线调动,他冲锋时常常忘了自己只是警卫员。朱德笑过:“娃子跑得比子弹快。”也正因如此,1932年草台岗战斗里他左臂中弹截肢,缝合时一句“少一条胳膊照样打仗”,让军医差点把针掉进伤口里。
1933年,红一方面军将“小军小师”改为“大军大师”。兴国模范师扩编成红六师,电报里直接点名洪超任师长。沙县一役,他率部强渡汀江,夺城、守城、再出城,手脚翻飞如常人。浒湾八角亭鏖战三昼夜后,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,同批名字包括张云逸、萧克、罗瑞卿。后台没有,人情也少,纯靠硬碰硬拼出来的牌面。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,中央红军被迫突围。陈济棠布下所谓“铜墙铁壁”第一道封锁线,纸面兵力三万。密令规定:敌不先动,不得开枪。红军顶层与粤方有口头协议,可双方基层互不知情,擦枪走火几乎不可避免。军团部需要一把尖刀天通盈,彭德怀指着作战地图:“让洪超先开路,他懂。”
于是有了百石的前夜。为了减少百姓损失,洪超提前派人劝集市暂停,信丰镇那天难得冷清。侦察参谋报告敌方增援迹象,他盯着地图捶桌:“不拖,一拳砸烂。”随后给黄克诚分工:“你带十一、十二团掩护侧翼,正面我亲自揍。”简单几句,部署清晰。

激战中,红十团翻壕沟、剪铁丝网,打进“万人祠”。守军负隅顽抗,洪超命迫击炮近距离压制。也就在这时,流弹击中他的额头。血染军装,他仍重复那个指令:“打到底。”最后一句话模模糊糊,只剩“别停”。炮弹掀起尘土,掩住他的声音。
战士们临别时请百石村民陈观音帮忙安葬。棉衣当作谢礼,墓就选在围栋山腰,草草堆起土包。陈观音不知坟里是谁,每年清明却都来上一炷香。几十年后,陈观音之子才从政府工作人员口中得知,山坡睡着的,是红军第一位在长征路上牺牲的师长。
2005年,新田镇重修陵墓。张震题字,碑面四字——“洪超烈士”。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兵站在水泥台阶上,抬头望半天,眼圈红了又悄悄擦干。碑前没有长篇致辞,只有几个再普通不过的鞠躬动作。

长征途中,师职以上指挥员倒在雪山草地、河谷关隘的不下八十人,洪超只是最早那个。可在彭德怀的生命尽头,他却成了唯一被郑重提起的名字。原因无需繁复注解:25岁的洪超,用一条臂膀扛起一座缺口,用一场顽战为三军团撕开活路。岭南秋风很快吹散硝烟,可许多老兵一闭眼,仍能看见那个少了一只手臂却挥刀冲锋的背影在前面。谁敢忘?
2
胜亿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